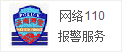中国有很多俗话形容不吸取教训的人,如“好了伤疤忘了痛”,“记吃不记打”,大概说的就是我。这不,几天前我刚在大理发誓再也不跟团,今天就突然忍不住,又加入一个四人散客小组,齐齐奔赴那诱人的所在——泸沽湖。
泸沽湖古称鲁窟海子,又名左所海,俗称亮海。纳西族摩梭语“泸”为山沟,“沽”为里,意即山沟里的湖。泸沽湖俗称“女儿国”,位于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,为云南丽江永蒗县和四川盐源县共有。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,是属于云南这半拉的,一个叫做落水的小村。
早在丽江热之前,泸沽湖就已声威显赫,天下知名。它的卖点很独特,据说沿湖居住的摩梭人 (纳西族的一个支系)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母系氏族群落,号称“母系社会活化石”,再加上它“男不娶、女不嫁”的“走婚”习俗,更为它的诱惑指数大大加了分。于是就有一拨拨的游人,压抑着暧昧的渴望,兴致勃勃地前来考察、参观、验证、猎奇,有志气的,甚至还暗藏了猎艳的野心。
从丽江城到落水村,大约两三百公里,都是艰难的盘山公路。汽车轰轰烈烈的颠簸,屡次覆盖了导游疲倦的声音。
导游是个神情冷漠的女孩子,不知道为什么,她似乎对彝族人很有偏见。汽车刚启程,她就告诉我们,除了上厕所,路上最好不要下车,因为一下车就有彝族小孩拉着你讨钱,不给就赖着不走,甚至躺在车轮底下威胁。况且彝族人一生只洗三次澡(时间分别是出生、结婚和死亡),所以他们身上还有种奇怪的味道,让人痛苦。
这些还算好的,更可怕的抢钱和讹诈。彝族人一般都住在高山上,这条路两边的山顶,大都是他们的聚居地。所以就有一些彝人从山顶吊下一只篮子,拦住汽车,让游客和司机向篮子里投钱,如果不从,彝人就会推下大石,砸坏车顶。讹诈的事也时有发生,就在上个月,他们的车不小心压死彝族人的一只老母鸡,竟被揪着赔了五百元,而在当地,一只烤全羊才卖四百块。没办法,谁让这是他们的地盘呢;于是车上四名游客和司机只好每人掏了一百,才得以放行。
大家一边听一边叹息:难道这就是阿诗玛、阿细跳月和烟盒舞的彝族吗?我不信。于是劝她道,那些坏人只是一小撮,大部分彝族人民应该还是清纯善良的,我们不也曾听过不少关于彝族的美好故事和传说吗?况且,彝族是云南25个少数人民中人口最多的,这么多的人,总不会个个都坏吧。导游漠然道,你们说得大概也对,但彝族的穷和落后是不能否认的,不信,你们想想,云南这么多的彝族人,可曾出现过一个名人吗?我们思考了半天,终于找到一个“彝人制造”,却被导游一声冷笑批判道,那是四川大凉山的。
说完这话以后,导游一路上再也没有开口。我们心里有些怪她冷淡,但后来得知她每月工资只有200元,就用怜悯替换了不满。再说,她言谈那么偏激,还真不如让她一边歇着。
车上的游客共有四名,除了我和老马,还有一对广州来的青年白领,是新婚不久的夫妻。无论年龄还是体积,男孩看起来都比女孩大了一轮。于是为了方便起见,我们把他俩分别称做老粤和小粤。
虽然都很健谈,但老粤和小粤的发音各有特点。老粤的每个字都带着浓浓的广东味,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他说的是鸟语。小粤则是标准的官话,有时还不小心跳出几句京片子,拖累她不得不屡屡向人解释她不是北京人。于是感觉小粤远比老粤聪明。这让我想起大学时代的两个同学,一对四川来的情侣。两人都分不清普通话中的前后舌音,但不同的是,男孩大舌头,女孩却过分的舌尖嘴利。于是当我问他们仙乡何处的时候,女孩的回答是“四cuan1”,男孩则是“shi4川”,虽然都是错,但女孩似乎比男孩伶俐了许多。
据两粤汇报,他们两人本来都是IT精英,曾经阔过的。网络热退潮后,大浪淘沙,卷走了高薪、光环和优越感等美丽的泡沫,却留下了嬉笑怒骂的网络精神,作为网络发展史上唯一贵重的遗产,日日相伴,来抚慰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。
因为刚刚结婚的缘故,他们之间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。两人不仅殷勤地把对方的照片喷绘在自己手机壳上,还四处炫耀,很是甜蜜。我拿过手机一瞧,发现小粤在照片中吐着舌头,而老粤则赫然坐在马桶上对着观众嫣然微笑。
显然这两人是有点意思的,有了他们,车上的空气愉快了许多。我愉快地和他们唠嗑。老马则是一如既往地玩深沉,几乎不说一句话,即使偶尔发现好看的风景,也只是用手指戳戳窗玻璃,再加上一个眼神提醒,仿佛他是一只被关掉铃声的手机,只设了震动。
午后时分,我们终于到达了落水村。村口突然出现几个脏兮兮的小孩,拦着我们非要兜售苹果,五块钱一袋,却只有干瘪的两三个。我们赶紧逃开,导游在旁边注解道:“彝族人!”语气很是得意,似乎在说,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。
走在落水的小路上,迎面看见一间叫做“大狼”的酒吧,导游说,它是一个广东姑娘开的。该姑娘原来也是个广州白领,偶尔来这里旅游,却不料在走婚舞会上爱上一摩梭小伙,没办法,只好在这里安家落户,顺便开了这间酒吧,继续他们的甜蜜梦想和幸福生活。“酸!”我们一边嬉笑批评,一边在心中暗问自己,是否敢有她那种率性而行的勇气。
酒吧的墙上挂着广东姑娘的大照片,穿着摩梭服装,肉乎乎的单眼皮,又白又胖,端的是个有福之人。仔细想想,我们不由都敬佩她的选择:与其在一个白领比白蚁还多的城市里庸庸碌碌,还真不如在美丽的旅游胜地变成一个风景和传说。这样看来,这个姑娘不仅有福气,而且还很有思想。
蔚蓝色的泸沽湖已在身边了。在导游的领导下,我们跳上一条猪槽船,开始在湖上晃荡。船头船尾各站一名剽悍的摩梭小伙,一边撑船,一边唱歌。歌声又高又陡,而且有一种挑逗的深情,显然他们是故意的。不知今夜的走婚舞会上,他们将成为谁的阿柱。这时我听到小粤低低的叹息,仿佛在说,这么好的人,可惜竟是别人的。
泸沽湖很美,不仅蓝,而且蓝得晶莹,蓝得沉静。虽然湖面有很多船,很多人,还有很多的浪花围着船舷跳舞,但船走过之后,湖水迅速归于无痕,丝毫没有浮躁的感觉。再看远处,却又发现湖面繁星点点,是折射过的七彩阳光,在微微的浪头上奔跑跳跃。
后来经过我在当地的采访,才知道泸沽湖的美,是和摩梭人强烈的环保意识分不开的。据说他们打小就被老祖母教导,不向湖中扔任何脏东西,也从不在湖中洗菜、洗衣服。即使后来旅游业带来了很多酒店和旅馆,它们的排污系统也不通向泸沽湖,而是通向大山;那些外地人带来的垃圾,都一点不留地埋进了深深的泥土。
木船靠近一个半岛,我们脱下救生衣,纷纷上岸。同时靠岸的还有另外几条船,于是我就问救生衣应该放到哪里,摩梭小伙慷慨地说随便扔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,但看别人确实是这样做的,而且来自不同木船的救生衣已经乱做一堆,好像根本不怕弄混,或者遭了窃贼。然后我突然醒悟过来,哦,原来旅游手册上极力强调的原始公有制,在这里竟是真的。
岛上有个“里务比寺”,好像是座佛教寺院。在这里,我第一次看见了转经筒和风马旗,它们是两种佛教用具,上面都印着经文。据说,很多教徒虽然不识字,但虔诚不减,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这样一种巧妙的策略:把佛经印在转经筒和风马旗上,每当人们转动转经筒,或者当风吹动风马旗,就代表他们念了经。呵呵,以前我一直以为宗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东西,到今天才知道它也允许取巧,也有人性化的成分。
划船回来,导游安排我们到一个摩梭人家家访,那也是我们当夜住宿的地方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摩梭人家,有高大的木楞房,宽敞的四方院子。进了院门,右手是传统的摩梭木屋,我们体验摩梭风情的地方,也是他们表演传统的舞台。左手边开阔的场地上,有越野车一辆,角落的柴堆上随意挂着几套鞍鞯。正屋大概是主人生活的地方,完全现代装修,豪华得像个星级酒店。临街两层十几个房间,则用作客房,容纳我们这些好奇的心和偷窥的眼。
走进右手的木屋,我们围着火塘坐下,开始听这里的女人们讲述此地奇特的故事。摩梭人把火塘叫做“锅庄”,它连接温暖、食品、生命和神灵,天生一种神圣和煽情的气息。主持座谈会的是个中年女人,面容沧桑,眼神却还是欢喜的。我们照例提了几个关于风俗和文化的问题,比如走婚到底是不是真的,这里是否实行计划生育。主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常规作业,便严格按照旅游手册一一做答。显然她是个优秀的摩梭文化发言人,她的回答严密圆满、无懈可击,但我们从中却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资讯。
会议结束,屋子里突然呼地闯进一排四名少女,原来下一个节目是摩梭少女为客人敬酒献歌。酒是当地特产的青稞酒,名唤“苏里玛”,甜中带辣;歌是当地特产的摩梭民歌,更是辣中带甜,句句都是“小阿哥”、“小阿妹”。慢慢地我发现她们的歌词中经常出现一个短语“马大咪”,便问是什么意思。一个长发女孩说是“我爱你”,外地游客学得最快、用得最多的摩梭语,有时我们一天能听到一百多遍,连家里的猪听着都烦了。满座哄堂大笑,纷纷赞叹该女孩真不愧是辣妹。
于是老粤站起来向她敬酒,女孩为保存实力,扭捏着不肯喝。老粤不依不饶,女孩被逼得狠了,突然眼珠一转,计上心头,道:“要我喝酒,可以。但是你必须给我唱歌,唱我们摩梭人的歌。刚才是我唱歌,你喝酒;现在既然要我喝酒,那唱歌的就轮到你了。”
老粤是个从不怯场的人,即使是个音乐盲,他也要凭借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,把歌词给背诵一遍。等他将“小阿哥小阿妹”朗朗背完,大家已经笑得东倒西歪。老粤面不改色,对大伙抱拳谢道:“献丑献丑。”傲然四顾,一脸的踌躇满志。摩梭女孩看着他,眼神温柔含笑。小粤便有些着急,轻声呵斥老粤别闹了。
然后摩梭女孩问大家老粤唱得好不好,大家说不好,强烈要求摩梭女孩亲自教老粤唱歌。人心所向,老粤只好同意了,但有个小小的要求:既然歌词他已学会,就不用再麻烦,他只需学一下旋律和调调就可以了。女孩含笑默许。于是女孩一句句地唱歌,老粤一句句跟着哼哼。剩下的人则一边观摩现场教学,一边争相指挥评论,做专家状。一时满室欢笑,宾主尽欢,女孩喝酒那茬事,早被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该吃晚饭了。我们来到正屋的时候,满满一桌菜已经摆好。屋角的电视兀自热闹着,正播放摩梭歌舞的VCD,一样还是“小阿哥小阿妹”。另外还有摩梭锅庄舞,据说今晚的走婚舞会上会用到的,我们可以先预习一下热热身。摩梭少女们匆匆吃了几口,就退席换衣服去了,为晚上的舞会做准备。她们似乎永远奔忙在摩梭文化的巡展中,哪些是生活,哪些是表演,在她们这里已经纠缠不清。
“猪膘肉”是摩梭饮食的一道大菜,它不仅样貌晶莹,味道肥美,还有重要的象征意义,相当于汉族年夜饭里年年都有的那条鱼。除此之外,猪膘肉还是摩梭少女成年礼上的必要道具,当那时,母亲给女儿穿上百褶裙,然后女孩双脚踩着粮食和猪膘肉,可以保佑她将来一生吃喝不愁。
然后我了解了一下猪膘肉的制作工艺,大体是一头猪去掉内脏,把剩下的部分缝起来,然后用盐和其他调料腌一下,再挂在当风处经历几年风吹日晒,便可以合格竣工。这种木乃伊,其实就是我国多族人民都喜闻乐见的风干肉,在昆明叫做“干巴”,在迪庆藏区叫做“琵琶猪”。
同桌吃饭的还有两个艺青模样的汉族小伙,好像也住在临街的客房里的,一上桌就跟摩梭女嘻嘻哈哈,似乎他们已然很熟。我便问:“你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?”“好多天”是我刚从老马那里学到的湖南方言,是问“多少天”的意思。只见两人谦逊地答道:“不多,才住了三个多月。”
晚饭后,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,那便是我们蠢蠢欲动盼望已久的锅庄舞会。在那里,我们可以亲自加入成群的摩梭男女,丢丢人,跳跳舞;况且,导游还一改一贯的冷艳作风,调皮地强调:“可以走婚。”
大伙兴奋着,带着半信半疑的眼神,却又不再追问。作为娱乐业一支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,旅游业早已领悟了娱乐的精髓,其从业人士,语言风格莫不虚虚实实、真伪难辩。所以对导游的话,我们都报以姑妄信之的宽容。在这种人人无所谓的空气中,如果较真,倒显得有些不识时务。
舞会是在附近一个大院里举行的,我们到达的时候,舞会还没开始。正好旁边有个“摩梭民俗博物馆”,就进去走马观花。里面展品不多,好像博物馆还在建设中。暗淡的灯光中,我们看见了巨大的老鹰标本,沧桑的牛羊头骨。还有一些锈迹斑斑的铁器农具,是热爱家园的有心人,从正在流失的传统中抢救出来的战利品。虽然许多传统因旅游业繁荣而枯木逢春,但那些没有盈利价值的传统,比如铁器农具,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冷眼和离弃。另外,我们参观时,正值一个来自京城的电视台在馆中采访,女主持人美艳无比,看得旁边几个摩梭小伙眼神发直。
忽听那边乐声大作,舞会终于开始了,我们匆匆跑过去。只见暗夜中一群闪亮的摩梭男女,手牵着手,或者牵着前面那人的腰带,踏着笛声,走成一条圆形的长龙。女孩身穿长长的白色百褶裙,衣衫鲜艳,头上的绢花簇簇火红。男孩则毡帽皮靴,斜襟的绸缎上衣,跳动颗颗闪烁的繁星。今夜的锅庄无比的雀跃,熊熊的篝火中,燃烧着心照不宣的快乐心事,和交错辉映的闪亮眼神。不知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,都将在这样的夜晚发生,篝火的舞蹈更加诱人了,仿佛在说:只要你愿意,只要你能够,爱情的空气人人有份。
夜色撩人,心事暗涌,一双双拘谨的眼睛跃跃欲试。狂欢本不是我们的气质,但在这诱惑的夜晚,我们终于决定把日常的自己迷失。
首先冲进去的是老小两粤,然后是我;最后,连一向跟浪漫有仇的老马,也被月色吸引,加入这跳舞的人群,跌跌撞撞地追赶众人飞翔的脚步。
确实是飞翔。摩梭人的舞步节奏很快,在笛声紧凑的韵脚中,他们仿佛是一边跳舞,一边奔跑。在这样的百忙中,他们还要拨冗寻找可爱的人,心中的小阿哥小阿妹。但因为练得多了,他们丝毫没有慌乱,反而越走越熟。而我们就逊色多了,学会了跳舞,却跟不上笛声;学会了奔跑,又忘记了舞步。于是推推搡搡地,在喘息和晕眩中,我们的激情和兴奋顾此失彼。
有那么几分钟,我身后来了个多情的大妈,因为步履艰难,她总是不住地拽我的腰带。当时充做我腰带的,是我在丽江刚买的土布披肩,宽大粗笨,所以很容易松散。于是那位大妈的手,不仅拖累了我的步子,还迫我不得不屡屡停下来,重新把腰带束紧,实在是恼人。后来趁笛声稍慢,我立刻摆脱了她,向年轻力壮的人群飞奔。这时眼前有镁光闪过,好像有人在进行风情摄影。
此时队伍前边牵我手的,是个高大的摩梭少年。舞会之前,导游曾告诉我们走婚的游戏规则:如果你喜欢某个人,就轻叩三下他的手心。如果对方对你也有意,则回叩三下作为回答;如果无意,就不理不睬,于是你就该静静地走开,无需继续纠缠。
我希望我这个错觉是真的。在某一瞬间,我感觉他似乎叩了我的手心,还没等我回答,队伍突然又飞奔起来。恰逢我的披肩又后面的人拉散,我只好暂离队伍,重新系好。待我回头再找那少年,已是芳踪无觅,仔细在队伍中搜索,只觉得每个人都像,但每个人又都不是。
于是我呆呆地站在队伍外,有些茫然。这时我看见了小粤,似乎也在焦虑地寻找着什么。一问,原来是老粤不见了,我开玩笑说,他大概找白天那个长发小阿妹去了,小粤立刻紧张起来,旋又柳眉倒竖地安慰自己:“他敢!”
群舞慢了下来,下一个节目是对歌。先是摩梭男女对唱,曲目仍是白天那些“小阿哥小阿妹”,我们都有些腻了。然后就开始真正热闹的部分,游客和摩梭人对歌。
游客们显然不是摩梭人的对手,因为人家是专业人士,我们只是偶尔来一次友情客串。再说,摩梭人的声音实在太高了,所以光在分贝上就轻易把我们比了下去。摩梭人在音量上的先天优势,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。因为摩梭人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湖边山上,所以对歌时需要隔山歌水地吼,扯着嗓子的,日子久了,嗓子自然越扯越高。
有游客反对道,光唱你们的歌,对我们不公平。于是又开始竞赛流行歌曲。但是天可怜见,原以为在流行歌曲方面我们要占绝对优势,但真到了考验的时候,却发现我们不仅不能完整地唱全一首歌,而且连歌词都记不住;有时本来能唱下去的,但是因为人多,突然有些害羞,就磨磨蹭蹭地企图放弃。对方的摩梭人替我们着急,实在忍不住,就帮我们唱了下去,终于鼓舞了我们的勇气和音量,然后更多的游客加入这合唱,混混沌沌地热闹起来。然后我们悲哀地发现,我们这些来自文明世界的人们,在表达感情方面,原来竟是如此的懦弱无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