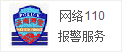去雨崩,我是随了网上的大流吗?
去雨崩,是由于时间还算宽裕吗?
或只据说,雨崩是个美丽的地方……
去雨崩,多少还因为一点面子和谈资罢
所有这些,都在我去雨崩之前,似是而非,不甚了了……
雨崩,是我中甸、德钦之行的最后一站。车驶出飞来寺那条街时,已经快中午了,早上的雪山观客早已各奔东西,梅里十三峰,仍在云卷云舒中时隐时现。卡瓦格博的峰顶在蓝天的衬托下,分外清晰,我的心情,也由于这个早晨的天公作美而格外晴朗。
从飞来寺到西当温泉,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。路上看到在峡谷中奔淌的砖红色的澜沧江时,有种惊讶,因为想象中这条著名的河流好像应该是青绿色的,尤其是当她流淌过西双版纳绿色原始丛林时的样子,如果不是亲眼得见,很难相信眼前这种干热河谷的景象。其实,在奔子栏看到的金沙江,就和在石鼓镇的江水很不一样,金沙江畔在石鼓镇所呈现的,是高原江南一般的风景,而在奔子栏月亮湾光秃干燥的山体衬托下,展现的则是一种质朴苍黄。
如果旅途之于你,不是匆忙从一个标志性地标赶向另一个地标的概念,那么留意在迪庆的行程中,由于海拔的起落所呈现的山体地貌,河流乃至植物种类和高矮的变化,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尤其在秋季,会让你一天内刚经过绿意盎然的森林,便进入直白裸露的铁灰色岩石山岭,然而 翻过一个垭口或是转过一个山弯,就有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迎面扑来,在一座座雪山山峰的映衬下,分外绚丽。
从西当温泉,走入雨崩的行程就开始了。出于对12公里上坡路程和1200多米海拔落差的综合考虑,我决定不要把自己的体力消耗在进雨崩的路上,于是选择骑马到的海拔3700的南宗垭口,然后步行下山,直奔下雨崩。一路上来或在向阳的山坡上行进,远眺云里雾里的白茫雪山,或在大树参天的原始森林里盘转而上。虽然把胯下的马累得够呛,倒却使我好整以暇,得以将沿途风光尽扫。
6公里的下山路,自然轻松。路上,居然又看到梅里雪山卡瓦格博的侧影,峰顶奇迹般地仍在视线中,这个距离让我意识到自己几乎到达了梅里雪山的脚下,对雨崩的概念突然有了一点感觉。离开了飞来寺,但我们没有离开梅里雪山的神界,雨崩,好比是一道门,或一个更近的驿站,使我们更加亲近梅里雪山。
拍了一张在绿色山谷中的下雨崩村,宁静,美丽,但似乎并不令人惊叹。
作为神瀑客栈当天最晚到达的客人,在微黑的傍晚我们甚至没来及辨清方向和环境,就草草地落宿,吃饭。神瀑客栈,如其名,是通向神瀑方向最近的打尖地点,对计划去神瀑的人,住宿这里是最好的选择。
这一夜,一向外出从无择席毛病的我,居然难得入睡,于是半夜12点多,终于忍不住穿衣下床,推门出屋。却不料一轮皓月当空,白光遍地,这般近的月亮,这样清冽的空气,如此安详宁静的村庄,于全无睡意的我,真不知是一种辜负,还是应该庆幸自己没有错过。
也许是头天的天气过于完美吧,大自然也常常是要平衡赐予人类的,第二天的清晨,就在云雾弥漫中开始了。我可能总共也就睡了不到三个小时,6点钟的时候就醒了。隔壁的三个年轻人,早早地起了床,开始商量当天的行程,因为房间之间只是木板相隔,左邻右舍的动静都会非常清楚。
其中一个小伙子的一句话,颇有意思,他说凡是进来雨崩的人,都不太会是平常之辈。我心里一动,为什么要来雨崩的问题,第一次浮现,而我,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。其实,雨崩在网上网下的驴友口中,似乎成了一个必去的标志性地点,这个标志,几乎可以是驴友和普通观光客的分水岭。不信由你,所有到过雨崩的人,不管他是骑马还是徒步来的,都会很有资本地对租车到飞来寺一夜,次日看梅里雪山,明永冰川后返归中甸那种游客和方式,不屑一把,因为他们不够“专业”,也不够酷。
做行程安排的时候,我曾在碧让大峡谷和雨崩间摇摆,后来一个做咨询公司的朋友说,去雨崩村吧,很好,我去过,可惜去神瀑时间不够了。
嗯,到梅里雪山弃雨崩而不入,对我这个自认为是半资深的行者,还真是说不过去。
早上9点多钟,客栈里的人,基本都走光了,我和同伴仍在廊下的长凳上,悠闲地喝着咖啡,看着白色的雾气在周围的山坡上聚合离散,安享这个湿润宁静的早晨。我们这样不紧不慢的节奏,曾令热中师傅很不适应。他说以前坐他车的人,总是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,急匆匆地起早赶晚。
我说,人在路上,时间永远不够,与其赶路,不如信步。
不过,通向神瀑的路,可就不是信步那样简单。从下雨崩出发后最初的一段,是穿过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,从平缓过渡到登高,坡度渐陡。森林中有些路段由于雨后一直得不到太阳照射,又总有牦牛或马匹不断踩踏,而成为烂泥地,混杂着牛粪、马粪,几乎无法落脚,只能硬着头皮踩着泥水走。 而当天从早上开始就在下雨,时大时小,幸亏我的衣服防雨性能还算完善,不然结果一定会很难堪。
从海拔3050米的下雨崩,到3400多米的神瀑,落差并不很大,但因为是身在高原,每一次呼吸与每一个步伐的协调变得格外重要,否则就会很容易觉得疲劳无力。我一般的做法是刻意在吸气时迈右腿,呼气时迈右腿,并且大声呼吸来强制自己节奏的一致性,这样做很有效,在形成了呼吸和脚步的惯性后,我竟一气走出了原始森林的路段而没有停下来休息。
原始森林后是开阔的高原山谷,植被丰富,雪山上的溪水或缓或疾沿山坡林间流下,汇成雨崩河,这条河流会流过雨崩村,流过尼汝,最后汇入澜沧江。 出了原始森林后不远是中途休息站,有藏民经营方便面,酥油茶等,据他说到达这里已经完成了全程7公里的三分之二,不由令我欣喜,因为过去的这三分之二的路程似乎还算很轻松。
没想到的是,这最后的2公里多的山路,才是真正的“杀手”。 首先坡陡至少达到50多度,其次是持续上坡,几乎没有什么缓冲路段。如果从下雨崩开始是骑马上山,那么从这里开始即使骡马也都止步,对体力的考验在这段才算开始了。 尽管这最后2公里的艰难程度,远大于前大半路程的总和,但我仗着一路走来对高原空气和呼吸节奏的适应,虽然常会停下来休息片刻,最终还是攀上了神瀑正对的高坡。
其实,神瀑本身不是什么壮丽的景观,一注冰雪融化的水流,从斧劈刀切一般的高高峭壁上,笔直而泻,然后汇成一个浅浅的水潭,蜿蜒着又继续流下山去,最后汇入雨崩河。与其说为景,倒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仪式的地点,因为这是藏民朝拜必去的几个典型的地方之一,不但周围藏区,还有西藏、四川的藏民都会迢迢跋涉而来,朝拜他们心目中的神瀑,神湖。
从神瀑对面的高坡向左下方看,是梅里雪山缅茨姆女神峰脚下的冰川,从女神峰呈舌状一直延伸到山脚,冰川的尽头,水嘀嗒融化着汇成一股溪流继续向山下流去,仿照再说长江的说法,那就该是雨崩河的正源了。
天仍在下雨,虽然这已是梅里雪山脚下,我所到达的最亲近她的地点 ,但女神峰云雾弥漫,不能得见芳容。不过好在昨天早上自飞来寺已经尽睹梅里十三峰的雄姿,所以倒未觉遗憾。先行上山的人陆续都离开了,我径自找了块石头坐下,按照我旅行时惯有的不紧不慢,看着眼前山口弥漫的云雾和脚下灰色的冰川开始发呆。
神瀑,可能在藏民心中,蕴藏着神圣而奇妙的力量。 我不信神,但我仍千里迢迢,辗转而来,又是为了什么?
周围非常非常安静,除了近处水瀑坠落水潭,和远处冰川融流成溪水的声音,后来甚至连这些声音都在我的意识中渐行渐远。这种空旷苍凉的感觉,就这样渗进我的心中,让魂灵开始飘浮不定,但却摇曳出被放逐的欢喜。
雨仍然没停,还时大时小,周围湿气很重,我渐渐觉得湿寒之气侵入我的关节,尤其是以前因徒步下山而伤损过的右膝,开始隐隐作痛。 这种熟悉的痛感打断了我“羽化登仙”的缥缈梦,面对7公里的下山路,保护我的右膝成了首要任务。
从下雨崩到神瀑,上山一般会用2.5小时左右,但我下山足足用了4个半小时。 因为只有慢,才能以最小的对地面的冲击力,对膝盖施以最大的保护。 这种慢,连信步都不如,简直就像一个游荡在山林之间的魂魄。 据走在前面的同伴玩笑说,他每每回头,就远远看见穿着红色冲锋衣的我,像一只红色瓢虫,在一幅天然而成的山水画布上,缓缓“爬行”。
不过,这种飘游的节奏也给了我最大的时间和空间,细细地留意起上山时因赶路错过的沿途景色。高原牧场多彩的秋叶,深红,金黄,橘粉,陈绿,或娇艳,或含蓄,错落有致,在白色的雨雾衬托下,宛然神秘桃源。 原始森林中,几乎所有的树干都覆盖着一层碧绿的青苔,笔直高大、需数人合围的大树比比皆是,溪流穿过森林,绵绵不绝地翻涌着白中透青的浪花。 如果不是因为呼吸着清冽凉爽的空气,让人会几乎以为是行进在常绿不衰的热带雨林中。
就这样,我时而驻步远望,时而低头缓行,时而偏离小路,只为去看一株红叶,或为追踪几步溪水的踪迹。 蓦然,我意识到世界原来可以会是如此空灵寂静,而我,居然也可以走得如此飘浮,飘得思想和逻辑都散了架,有那么一刻,我甚至希望自己的魂灵能在这森林中永远这样飘摇下去。
我们何必,急急忙忙从一个目的地赶到另一个。每一次这样的旅途中,我所碰到的大多数的旅行者,似乎都是这样。 他们的原因似乎也可以理解,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宝贵的一个星期,十天,两个星期,对于一年甚至数年的工作奔波,实属难得。不过如此一来,匆忙紧凑的行程竟成了对难得休假的过度补偿,难道我们在城市的躁动和压力下,奔忙得还不够吗?
曾经收到过一个在公司里广而转发的邮件,题目就是:别让你的灵魂赶不上你的脚步。
我之所以,封自己是个半资深的行者,就是因为只走别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行程,而想把剩下的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的灵魂。
回到客栈的时候,已在雨中晃悠了8,9个小时,我相信自己一定是最后一个归来的游魂。 真得感谢身上的防雨装备,否则灵魂的洗礼就得连累身体受罪了。
这个晚上的神瀑客栈很热闹,因为这个日子,山上放牧长达月余的牧民们,赶着牦牛离开牧场,回到家中。归家的温暖和喜悦,似乎洋溢在村子的空气中,宁静的小村庄一下显得人丁旺盛。更多的旅行者也打尖在神瀑客栈,当中,还有一些从其它藏区长途跋涉而来的藏民。
神瀑客栈的餐厅和厨房就设在主人的房子里,里面除了主人的卧室外,还有一个很大的客房,估计是主人招待本族来客的地方。 和我所到过的藏族人的餐厅一样,当其他游客吃完饭离开后,饭厅里就成了藏族人把酒歌舞的场所。
一天在雨中的跋涉,让我对主人饭厅里一只炭火盆产生了极大的依恋。吃晚饭后就顾自在一个角落里没完没了地烘着衣服,不是因为湿,而是想去掉周身的一种潮冷的感觉,并且在火盆的温暖中,揉捏右膝以缓解酸胀疲劳。
那一边的歌酒游戏和欢声笑语,渐渐扩散到了整个房间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载歌载舞的欢快中,客人中来也有自告奋勇唱歌的,当然是那些能说藏语,唱藏歌的客人,居然还有一个穿着僧袍的喇嘛也会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唱歌的行列。
一个年轻的藏族女孩被推到中间,她看上去既普通又羞涩,但一张口,声音却是无比惊艳。藏歌所特有的高音颤音被她驾轻就熟,而且音准非常到位。刚才还喧嚷的房间竟然立刻安静下来。女孩的叔叔大概也是主人阿青布的亲戚,拿出藏族二胡,乐器的加入使大家舞蹈的兴致一下高涨,开始围着屋子转圈跳起了舞蹈,大家“来索,来索,呀擞”的喝呼之声此起彼伏,原来还不太熟悉的主客之间,客人之间,似乎都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并融化了生疏。
拢着火盆在角落的我,用些许羡慕,看着欢乐的人群,他们当中,有一走就是月余,今天刚刚从高山牧场回家的本村牧民,有远道而来朝拜神瀑的藏族男女香客,有给从其他村庄辗转而来的旅行者的藏区向导。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,但却从他们酣畅淋漓的歌声舞步中,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。
在这个离梅里雪山最近,离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最远的小村庄,在这个设施纯朴简陋,灯光昏黄的房间里,看着一群从不相识,甚至不曾交流,而明天分手后可能永不再见的藏族同胞,用我听不懂的话谈笑风生,载歌载舞, 我感觉到自己的时空发生了奇怪的转换。我的魂灵似乎随着我的视线飘出我的身体,悬浮在半空中,俯看着欢乐的人群。我试图透过他们快乐的眼睛,去看看他们不欢歌热舞时的烦恼,猜想那种烦恼会是什么。
不过我想,那一定是世间最简单直白的烦恼,所以他们才会有最简单原始的快乐。如果是这样,就算只拥有他们的烦恼,对我的生活来说,会不会就已经是一种奢望?
一种深深的惜别之情,从我的心底弥漫开来。 雨崩,这个在最初在我眼中,美丽但并不惊艳的小村庄,这个在我的行程中原本只具有某种标志意义的地标,这个我不甚了了而懵懂闯入的雪山脚下的世外桃源,在被雨崩的雨洗过,将神瀑的水喝过,在被秋色的斑斓和森林的碧绿陶醉过,却不曾料到,原来我千里辗转,一路而来最为动容的一抹亮色,却是今夜那一众原生原色的笑脸,和在歌舞笑语中饱含的,人性的温暖。
我知道自己,已经不会有和他们一样的快乐,因为我的心上,已经积结了厚厚的茧子,层层覆盖了最深处的柔软。但我并不想强求自己,去得到这种今生定与我无缘的感受。只要我知道这种最天然质朴的快乐仍然存在,并羡慕她被善良而朴实的人们快乐地拥有,即使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角落,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,我的心中也一样充满了温暖的感动。
这也是一种,几乎让我哽咽的感动,在不觉中,令我热泪盈眶!

(飞来寺看梅里雪山太子峰)

(飞来寺看梅里缅茨姆女神峰)

(去西当进雨崩途中看太子峰和脚下明永冰川)

(下雨崩清晨的白雾)